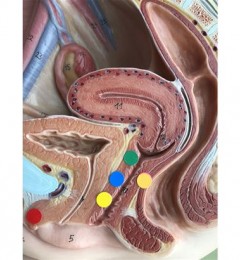在很小的时候,大概小学二年级,我就想过一个问题:下辈子要当男生还是女生?我忘了究竟是哪个事件触发了这个想法,但我记得当时心中的答案:男生,因为在那个时代,在我小小的生活圈子里,很明显的感受到男性是这个社会中的优势族群。
回想起来,其实成长过程中我是个饭来张口,茶来伸手的少爷。我的家境并不富裕,依稀模糊地记得有过一阵子家庭代工的时期,那时家里有一袋又一袋的手工活儿,如果妈妈在忙的话,就由我们这些小孩在宝利龙球上黏贴眼睛,或在小拐杖上缠绕花花绿绿的铁丝,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是圣诞树的装饰,不过我们家从来不过圣诞节,妈妈所在意的,是妈祖、关公或佛陀的生日,往往到了拜拜的时候,我就巴望着供桌上的黑松沙士与乖乖,希望神明们快点吃饱,然后可以换我吃。
我是家里最受宠的小孩,如果今天餐桌上有猪脚、鸡腿、或鱼肉,妈妈会先在我的碗里放一块,其余的人则自己夹;餐后我从来不用洗碗或整理桌子,妈妈只催促着我快去洗澡念书,其他的由姊姊、妹妹处里,而她们跟我一样要应付回家作业与隔天的考试。

十岁的时候我的班导师也兼差教钢琴,一天她来我家洗头,聊着聊着就决定开始学钢琴了。刚开始的进步很慢,因为家里没钢琴练习,拜尔上册我弹了一年还没学完,然后有天夜里,我正上床准备睡觉的时候,听见楼下传来乒乒乓乓的声音,于是起身躲在楼梯扶手偷看,只见在不到一公尺宽的楼梯间里,一群人正满头大汗地搬着一台钢琴,小心翼翼地将那个庞然大物搬上楼。第二天我满心欢喜地起床,看着晨曦透过落地窗,穿过空气中飞舞的微尘,照射在那部价值八万元、黑得发亮的美丽乐器,沈稳又庄严地座落在客厅的一角,默默地等待我雀跃的手指,掀开它厚实的琴盖,温柔地触碰它黑白分明、滑顺而散发木头香气的琴键。
那是1984年一个既惊喜又魔幻的时刻,在那个物资并不丰裕的年代,拥有一台钢琴是个连做梦也不敢想的奢望,而我的父母,像魔法师一般,变出我童年时代的南瓜马车。多年后我才明白,那台钢琴散发的光芒,不单是晨曦的反射,而是父母燃烧的青春光辉,温暖、坚定又内敛地洒落在那个微温的早晨,许我一段长长的幸福无忧时光。
我从来没想过成长过程中姊姊妹妹的感受是什么,自有记忆以来,我似乎在家里就拥有特别待遇。在学校中也是这样的氛围,我记得国中同学曾对我说过,为什么都是男生当班长,明明女生也可以当啊!有一次地理作业是画一张台湾县市图,发回来的时候,老师在全班面前夸我画得很好,给我满分,女同学不服气地拿来看,嘟囔了一句:到底是好在哪里?说实话我也不晓得,只是处于飘飘然的状态。
在这样集体潜意识所形成的社会价值观中成长,我以为男生只要愿意分摊家事,对女孩子温柔贴心,就算是稀有动物了,这些“自以为”的想法,像大树的根无声地蔓延生长,又紧紧地盘结在大脑深处,而我的言语、行为、态度就是向外蓬勃伸展的枝叶,表现在我跟异性之间的互动。
我很怕跟异性吵架,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对方生气的点在哪里,而当我一昧地安抚道歉,企图大事化小、小事化无的时候,结果往往适得其反,爆炸的震波会晃得我脑袋一片空白,只想就地掩蔽。我不讳言在婚姻里,有长达6、7年的时间我不知道怎么跟老婆沟通,感觉很多时候球投了出去,但只是擦板后被篮框弹出,一直无法破网得分。在主观的意识里,我觉得为何她不能了解我的想法与试图理解的努力呢?为何她总是有很多的质疑与批判,试图撼动这个社会对待男女的倾斜天平呢?为何不能改变自己的态度融入这个世界呢?
直到生病的这两年,当我的生活步调放慢,有机会好好梳理自我内心的时候,我才发现原来是我的问题。
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里有一段夫妻吵架的情节:
“金智英觉得十分心寒,因为自己遭人误解身体有缺陷时,丈夫竟闭口不语,对此郑代贤的解释是,他担心要是帮金智英说话,只会使事情愈演愈烈,但是金智英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说词,郑代贤则认为是金智英太敏感,过度解读长辈的好意。”
我有点不忍卒睹的羞愧,这真是直白地描写出某部分我的心态。有时两人在面对外界的观感或压力时,我以为自己是在顾全大局,尽力让导火线不要延烧,但说穿了其实是乡愿,下意识忽视了对方的感受与求助,反而认为不用大惊小怪,只要心理调适一下,接受现况也就罢了。所以过去发生的擦边球是合理的预见,因为我从没有正视核心去投篮。
在《婚姻故事》里,在Nicole与Charlie双方与律师一同坐下来试图找出离婚共识时,Nicole很在意Charlie说了好久的“我们可以去洛杉矶住一阵子”的承诺一直没有实现,Charlie辩驳说那只是“讨论”,就像讨论今天去哪吃饭?买哪个牌子的洗发精一样平常,根本不是一个“协议”,Nicole的律师马上跳出来说:“所以这8年来,你的意见就是『协议』,而Nicole的意见就只是『讨论』?”
我老实说,这情节如同一根针沿着脊椎钻入脑袋,然后又在心坎上忽冷忽热地刺着。
Charlie那些不经意的想法、顺口而出的言语,流露出对男女不平等的理所当然:男人永远可以自我中心,不计代价追求成功的光环,而女人最称职的角色,往往是担任牺牲奉献,无声付出的背后推手。
我发觉Charlie的血液也在我的身体里奔流着,那些既定俗成的价值观及文化氛围,静静地随着岁月长河浇灌着在原生家庭、在学校、在社会成长的我,于是那些根深蒂固的自以为是,逐渐变成会扎伤异性的刺,然后伤人却不自知。这两天看着批评吴宗宪的言论在各平台炸锅,我心里想,还好我还保有一丝勇敢与反省的能力,得以在时代与传统的冲击下觉醒,逐渐蜕变成一个可以共感同理的人。
昨天是肺四确诊两周年,从一开始的惊慌失措,到现在内心的疗愈梳理,我感觉好似从冬眠中苏醒,重新觉知周遭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,慢慢窥见从过去到现在,在时间的磨损下自我存在的意义。
主治医师跟我一起看了上个月的断层扫描结果,肿瘤从4.4公分变成了5.8公分,他小心翼翼、怕我受伤害似的说:可能抗药了,再观察3个月看看。我问:接下来就是化疗了吗?他点点头。
所以,原本期待慢慢好转的消息落空了,我沮丧地坐在领药大厅呆看着数字跳动,平缓一下方才泛起涟漪的情绪,直到能够起身去柜台拿药的时候。
驱车返家,想听点音乐来转移心思,音响流泄出来的第一首歌,是萧敬腾唱的〈梦一场〉,于是我低声地啜泣起来。
这种苦甜搅拧在一块儿的时刻难得,又喜又悲的我决定要纪念这一天,于是前往新堀江,选了一个小巧的、微微闪耀的宝蓝色耳钉,喀哒一声,让它驻留在我的左耳。
我全然接受并且深爱这样的自己。
今天是白色情人节,祈愿我们都不要停止爱自己。